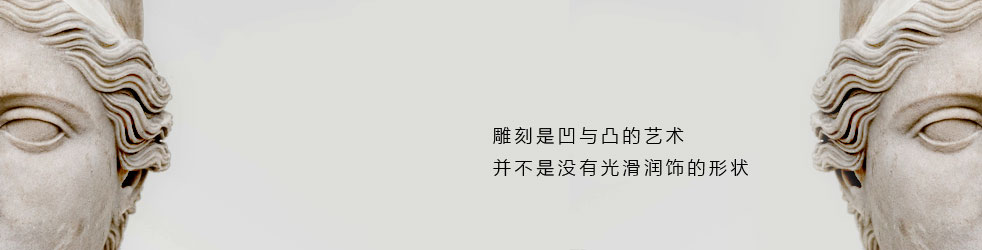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序
塑造生命——孙利平雕塑
张纯仁
孙利平的雕塑要出集子,让我写篇短文,我实在诚惶诚恐,一则我不是雕塑家,不懂其中玄机;二则不是文艺家,不能站在应有的高度审视其作品。仅是因为相熟得早,看见他一步步走过来,到今天。
我觉得他应该属于那种凭着感性摸爬滚打出来的人,起始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会去玩泥巴、搞雕塑。直到他突然看见米开朗基洛、罗丹和布德尔作品的印刷品(上世纪70年代这种东西还不多)。雕塑的体量感和生命力就抓住了他。他学着做了第一个雕塑——《忧闷》,作品发表在1980的《美术》杂志上,这对初学者建立信心无疑是很重要的,并因此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他从一个美术公司的普通员工调入刚成立的贵州雕塑工作室,作了雕塑艺术工作者。
上世纪80——90年代是贵州美术界最活跃的年代,乡土热和向民间艺术学习风刮遍了油画、雕塑、工艺美术等艺术门类。孙利平也在这段时间里努力观看、感受、摸索,为自己的将来寻找道路,积蓄力量,做了许多石雕、木雕作品。
有一阵子,他忙于室外雕塑、浮雕。那些东西在我的印象中并不深。当一个艺术家把商业因素作为首位考虑时,我认为它的艺术价值就会受到抑制,孙利平也不例外。
大约是进入新世纪前后的日子吧,孙利平约我去看他的作品,我去了,我迷惑了,他怎么弄出了这样一批东西?原谅我引用罗丹先生的话:“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恭喜上面能够发现出美来。”葛莱尔说罗丹的作品:“对生活、生命深深的爱引导他沿着这条路走着。我凝视他的作品,一种深入自然、渗透自然,与之同化的心灵的愉悦同时也侵袭了我。”这确实也是我当时的感受。感觉心里神奇一股温润的气浪。
单纯的人用单纯的方式切入自然和事物的内心。他不研究,也不刻意追求雕塑怎样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共进,他只关注人与自然,他们的和谐。
孙利平在他自己这条路上似乎走得很兴奋,几年间塑了几十件很有分量的作品,这些为自己做的东西赢得了普遍的好评和赞誉。我把它们称为孙利平为“自己”做的作品是基于他没有考虑商业价值和要引起过少社会效应。
很多观众说这批雕塑有“味道”。这个词含有复杂而不易明确的定义,但显然有作品中作者的个性和对“美”地阐释的肯定。
这是一批表现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山民的日常行为习惯的雕塑。雕塑没有古典的均衡比例,没有细腻光洁的“美”,也没有叙事的豪情。在大街小巷现实中我认为很“丑”的形象、已没有被物质化的心境引起我的尊敬和羡慕。他们放开心来,自自然然地生活——忧愁、快乐、健康,这是一种异样的、孙利平认定的“美”看艺术作品时观这很快越过形式表面而被某种东西吸引是很难做到的。孙利平做到了。我不知不觉沉迷在那些《龙门阵》、《困》、《醉》、《往事》、《老照片》、《山里人》、《走出太阳》、《北狂》……的人们中,产生于他们贴得很近的感觉。单纯、质朴、善良、心灵洁净的塑像引起我发自内心地笑、惆怅或振奋。孙利平不是旁观者,也不是高高在上对他们怜恤、批评、指导。他的心和作品中的角色的心里是坦诚相见的。他尊重他们对生活的选择。
虽然没有直接描绘塑造自然,我还是觉察到这些雕塑有一种扑面而至的山风。《渴》、《山妹》、《趣》、《午睡》、《三眼萧》……自然而然把我导入悠悠的山林、清澈的溪流和古老的板房之中。“越过形式”,气势正因为形式和主体的和谐统一,孙利平的雕塑语言内敛意赅,它摈弃细枝末节的真实,没有民俗研究者追求以装饰物的精细描摹,角色们粗衣土布,经年累月的穿在身上,和形体浑然一体。尤其是女性的纺锤形、长颈短腿、发辫(并不是贵州山民的)经夸张运用后一切都显得恰如其分。这只有艺术家用天分才能掌握的精确分寸感,不到以及过一点都易流于滑稽荒诞。
孙利平喜好强调手捏泥塑的特点,常常会误会他是一个从农村环境中走出来的艺术家,因为这里面蕴含着对泥土深厚的感情和熟识,正如他所言:“还泥土以生命。”一个自幼生长在城市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但他做到了。我很是喜贵州的山,因而也理解他雕塑的构图,沉稳险峻如山之悬石。总之,方方面面现露出贵州这片特有的土地给他特有的影响。
在他安静的小小的工作室中,几十座塑像把房子弄得很热闹,我坐在其中,不感孤寂,塑像以他们丰富的生活情趣把我带回到真正的人的世界。
孙利平还年轻,还有许多时日去塑造更多丰富的世界。他一定会走得更好更远,也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为他鼓掌,我相信。
发表评论
请登录